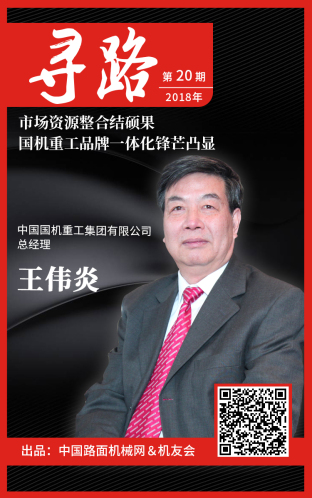VR电影的趋势分析:一个属于社群电影观念的打造
我们的世界里,只有我和你。“现在,我们是在电脑程序里?”这句台词是尼奥(Neo)的――在沃卓斯基兄弟编剧、指导和制片的大片《黑客帝国》里,基努・里维斯所扮演的尼奥。困惑的尼奥用这个简单的问题让千百万观众相信,虚拟现实能够如此真实,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自己是否正身处于虚拟现实世界之中。当然,《黑客帝国》只是一部电影,但是脑科学验证了沃卓斯基兄弟的许多设想。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样,只在后脑勺插一个插头就能把自己送进虚拟世界,但是沉浸式360°影片已然能带来更多、更真实的体验。
对于那些生活在理想虚拟世界里的人们来说,还会有些其他可能性。这些问题是美国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的主题。这部电影里,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因下肢瘫痪而被困在轮椅上的军人杰克・萨利,以进入一个虚拟身体的方式成了另一个种族“纳威人”的一员。用这个化身的手臂、腿脚和尾巴,他能跑过丛林,也能在树枝上荡来荡去,他甚至还能坠入爱河。
通过电影我们可以发现,通往真实与虚拟之间的介质其实是架构在《阿凡达》和《黑客帝国》故事创想上的一个媒,在这里不妨大胆地定义一下这个“媒”――“化身”。建立在“化身”基础上的原点,是虚拟现实社群电影的一个假设性开端,是将讲故事的权利转移到每一个真正经历这些故事的人身上。这也正呼应了虚拟现实的“4IE”的突出性质。当结合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摩擦出火花时,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超凡体验。
假设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大数据已经具备了足够分量的参考价值,每个个体单位的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如美好的回忆、有教训意义的回忆等,都有周全的数据备份,人们可以在大数据中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模型,这就为虚拟现实中的“化身”打下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虚拟现实导演就可以在社群电影上有无穷无尽的创想了。
以《三兄弟穿越时空的结拜》的VR制作逻辑为例。在现实中这三兄弟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偶然之间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回忆起了儿时结拜时的场景――家乡的那一碗“老友粉”。各自意识里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因粉结缘”。这时VR导演就可以进入半创作状态了,在搜集每位老人大数据身份模型的情况下,通过CG美术视觉,基于人工智能的店面服务人员的角色设定,三位老人“化身”的绑定,很快可以搭建起那个年代的视觉、听觉、触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符合导演所构想的状态。当体验架构制作完毕后,配套上及时的物流系统,将当时当刻的那一碗粉或者必需的道具尽可能地还原出来。在整个体系完成后,三位老人就可以通过戴上“VR装备”来进入历史时空,回到当年年轻时候的自己,并且可以彼此触摸,共同品尝当年同甘共苦的日子。同时家族里的后人,可以以灵魂视角的方式进入这个历史世界中,来客观地体会当年爷爷那个时候的经历。《三兄弟穿越时空的结拜》只是抛砖引玉,VR的脑洞可以无限深挖。
这样的一种假设,是基于观众视角思路的游艺性沉浸式戏剧化,导演只是搭建了这个世界和里边所呈现的元素,并潜移默化地以多种方式进行引导。最终将故事的叙述者交还给了观众,并使参与到里边的观众社群具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因为这个虚拟的世界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中关键部分的再现,自然会让观众产生共鸣。以后的电影,会更多地趋同于将故事的演绎权下放给观众,当然那时观众的属性也需要重新定义了。网络给更多人自由的权利,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是舞台的主角,“VR+”只是在媒介形式上提供了方便之门,使之参与到社群电影的大世界中,往后的票房方式会更加灵活,将会产生出新的虚拟现实影视生态。
新闻投稿:news@lmjx.net
相关资讯
VR在心理急病健康方面的应用案例
牛津大学精神病学部通过对牛津健康NHS信托基金会的病人进行研究,发现让病人在VR中面对自己害怕的情景可以帮助病人建立自信,发现自己所害怕的东西其实非常安全。
VR虚拟手术应用技术
虚拟手术的概念最早于1989年提出,即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指导医学手术所涉及的各种过程,在时间段上包括术前、术中、术后,在实现目的上有手术计划制定、手术排练演。
VR医疗应用案例
瑞典一家公司用VR技术做了一个专门用于医生培训的模拟人,第一代模拟人只能做心肺复苏,而如今已经可以预先对模拟病人进行编程、对复杂病情进行模拟,这种新的模拟人可以。
今日头条
- 小松:“转”动惊喜第一期 | 转出新效能,赚得新未来
- 智慧·绿色·延伸人类力量 | 柳工惊艳亮相BICES 2025
- 山工机械新品发布仪式于2025 BICES展会隆重举行
- 2025年8月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快报
- 高空科技战略联盟启动:驱动高空作业设备后市场价值升级
- 展前预告|中国路面机械网携 “数智营销利器”亮相BICES 2025,为您把握全球商机!
- 让施工更简单丨山推股份闪耀2025印尼矿业展
- 2025年8月起重机、平地机、高空作业平台等主要产品销售快报
- 以“智”赋能,柳工重塑小型工程机械新标杆
- 直播|9月12日17点,BICES 2025卡特彼勒展台亮点首发!围观领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