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李郁 1958年11月中旬,两名刚到柳州不到一个月的华钢厂工人在柳州火车站出站口张望。前几天接到电报说新厂筹建处的领导李郁今天要到柳州,可两人之前都没有见过他,只能按照自己心中想像的领导形象,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个月来,陆陆续续从北京、上海等地过来10多个人了,有的是刚刚结束在洛阳的工程就直接赶过来的,有的是先到茂名又再赶到柳州。由于是先遣部队,大家都住在市政府附近的一个澡堂里,这样既方便和当地政府沟通,又节约成本。厂址选在柳河西岸一个叫龙腾背的地方。名字虽然大气,但那里其实就是一片荒地,离市区要10多里的路程。前几天,市政府在一个钟表店楼上给厂里安排了一个办公场所。现在领导也来了,看来开工的日子不会远了。
两名工人分别站在出站口两边,遇到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就上前询问,但是眼看着出口处的人越来越少,却还是没有找到,直到出站口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时,车站的广播里传出了声音,在已经安静下来的出站口这声音显得清楚而刺耳:“筹备处接李郁的同志,到问事处来,有人找……”赶到问事处,一个身高体壮、穿着旧棉衣的“大胡子”已经站在那里了。一问方知,这个人就是李郁。看着来接他的两名工人,李郁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们真笨,不知道写个接李郁的牌子么?”被训的两人还觉着眼前的壮汉是个北京过来临时安排工作的干部,没想到他便是后来柳工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李郁是广东人,早年参加过游击队。解放战争结束后,又带兵在两广打了几年土匪,得到个“剿匪司令”的绰号。后被安排到中南建工局担任党委组织部长工作。打了小半辈子仗的李郁并不习惯办公室的生活,接到要去建茂名油矿的消息后,他立即开始北京、上海、茂名三地间奔走,建工部与上海市委的谈判李郁也参加了。
到柳州后,李郁先组班子,建立了工厂的第一个党支部。华钢厂虽然以生产钢结构为主,但具有一定的机械加工能力。所以经过与上级领导商议,将工厂定名为“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柳州市的领导亲自安排将柳州铁路局的俱乐部作为工厂的筹建处,从上海过来的工人和家属共计520人,都借住在柳铁宿舍里。有的三家同住一室,拉布为墙,其艰苦可见一斑。
□建炉大会战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柳州市也动工兴建了柳州钢铁厂。市领导找到李郁,问能不能给柳钢厂生产两座255立方米的高炉。李郁不怎么懂技术,但战争年代的经历告诉他: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不打场胜仗,队伍的情绪可能会不稳。而且,从上海来的老工人技术好、办法多,曾在长春、洛阳干过类似的活。于是,在不具备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李郁大胆接下了任务,决定和命运赌一次。
在动员大会上,李郁把这次任务命名为“建炉大会战”,激励工人干部打好进入广西的第一仗,柳工的第一次生产任务便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
他们边生产、边建设,搭起了芦席棚屋,作为临时车间。由于从上海、洛阳等地运来的设备堆在草棚里,没剩下多少空间。于是,又派一个小组到柳钢工地露天生产。时间紧迫,有的工人是刚下火车,还没来得及安家就直接奔赴柳钢工地投入生产。
广西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的地方,而1958年末的这个冬天雨水特别多,阴雨绵绵,竟日不停。在柳钢露天生产的工人白天只能在雨中工作,夜里躺在简陋的临时宿舍里冻得睡不着觉。由于缺少生产设备,“1号高炉”的很多部分完全是工人们抡着18磅的锤子一下下、一次次敲出来的。没有起重设备,就几十个人喊着号子把钢板推起来,再直接砸在地上,溅起地上的泥浆弄得人人混身上下满是泥水。在当年创业者忆来,那时的劳动中充满了欢快与豪情,并以吃苦为荣。
虽然经常停水停电、停工待料,甚至连像样的伙食都没有,但这批上海工人竟能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两座数十米高的炼铁炉耸立在柳钢厂内,广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动化的炼铁设备。市党政领导亲临现场,对柳工人的工作精神倍加赞赏。
“建炉大会战”是柳工在广西的第一场胜仗,而一个附带收获则是,上海老工人在厂里的威望大大提升,甚至直到今天,柳工的第四代领导人王晓华回忆起上海老工人都充满了敬佩之意。
□建厂安家,苦战三年 似乎是前一年把雨都下完了,1959年的冬天,柳州少雨。一年来,柳工已经小有规模了:共建成了四栋半土墙的宿舍,而单身宿舍和车间尚是削竹为墙,编茅作瓦。当年秋天,因为接到西津水电工程局一个生产闸门的任务,柳铁还给厂里修建了两公里的铁路专线。那时国家是执行计划经济,企业这些建设全是靠李郁和其他柳工干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来的物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
但前一段时间,有个消息也令厂里人忐忑:1959年9月末,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发现了巨大油田,足以一举摘掉“贫油国”的帽子。由于正值建国10周年,油田被命名为“大庆”。国家已决定全力开发大庆油田,而暂缓在茂名建厂的计划。谁也不知道柳工今后是否会有足够的生产任务,也有传言说柳工要与武汉建筑机械厂合并。
“建炉大会战”延续下来的稳定局面在这个冬天有些动摇了,更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11月9日晚上9时许,一场大火将刚建起来的厂房、宿舍化为了灰烬。工人们拼命抢出一些设备,但一年来的建设基本上没剩下什么。
看着一片焦土废墟,李郁哭了,老工人们也哭了。如果多点雨水,如果没有这六级偏北风,如果多点资金,不用茅草、竹子、油毛毡搭房子,如果那个工人不在屋里抽烟,就不会……现在,有的工人们连衣服都没抢出来,更不要说生产器材和设备了。柳工此刻真的有点不知路在何方了。
李郁当晚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商量安排善后事宜。11月10日下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游击队员出身的李郁在会上说,“这次火灾,我们没有失去一个同志。人都在,就没什么好怕的。大火烧掉的东西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只要人还在,我们就能再造一个柳工!我们就能把火灾的损失夺回来!”
随后,厂里下达了“三天之内‘马达转、机器响’”的命令,并提出“建厂安家、苦战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给第一代柳工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提起它,人们都不住的感叹李书记带给这个工厂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当五十年代随历史长河奔流而去,早期新中国工业的特征也愈加凸显出来,企业带头人是政治领袖,依靠凝聚精神来维系组织,用组织“战役”的方式创业,确有奇效。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50年前的往事,并向柳工最早一代创业者致敬!他们是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的一代产业工人,以战士冲锋陷阵的姿态从事工作,何等骄傲,何等豪迈!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50年前那个激情创业的柳工,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而是国家计划经济大框架中的一个棋子,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生力军。没有主导产品、没有供求链,但有上级主管和户头,需要等任务或争项目、领拨款或跑投资,与一个在市场中发育成长的企业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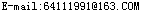 中国路面机械网是工程机械行业主流、权威的传播媒体。中国路面机械网的新闻资讯是百度、谷歌、新浪、搜狐等媒体的新闻源提供者,中国路面机械网所刊登的新闻将同步显示在以上媒体的新闻搜索中。
中国路面机械网是工程机械行业主流、权威的传播媒体。中国路面机械网的新闻资讯是百度、谷歌、新浪、搜狐等媒体的新闻源提供者,中国路面机械网所刊登的新闻将同步显示在以上媒体的新闻搜索中。